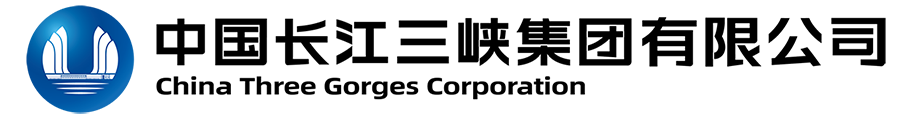

本網訊(謝澤 胡暉 汪文婕(實習))三峽工程是長江流域防洪體系的關鍵性骨干工程,使荊江河段的防洪標準提高到100年一遇。遇到1000年一遇的洪水時,三峽工程配合荊江分洪工程運用,可保證荊江河段防洪安全,避免長江干堤潰決。
三峽工程和荊江分洪工程是長江流域防洪體系的兩道重要屏障。這兩座世紀工程握手的故事,要從1998年那個驚心動魄的夏天說起……
1998:艱難的抉擇
1998年的夏天,長江猶如一頭被激怒的巨獸,狂暴地撕扯著中游的荊江大堤。
湖北省公安縣,據荊江分洪工程北閘管理所工程管理科科長陳小明回憶,當時他正經歷著職業生涯中最緊張的時刻。長江第二次洪峰向下游奔涌,沙市站水位一次次刷新歷史記錄,直逼45米的保證水位。
“準備分洪!”——一道來自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的命令,讓整個公安縣瞬間進入臨戰狀態。這意味著,33萬百姓和1.8萬頭牲畜,必須在20小時內完成轉移。
在距離北閘僅數百米的防淤堤上,119個爆破藥室里,22噸TNT炸藥已靜靜埋設,等待著最后的引爆指令。荊江分洪工程北閘管理所老干科科長付兵的任務是確保起爆電源的萬無一失。

▲1998年準備分洪時進洪閘防淤堤預埋炸藥的標記 攝影:楊津
“我們單位員工都撤到了兩公里以外,”陳小明說,“等到防淤堤爆破了以后,我們再跑過去開啟進洪閘。”
整個分洪區內,30多萬群眾攥著戶口本,帶著干糧,在干部與解放軍的護送下,告別即將被淹沒的家園。
陳小明的家在安全區內,他清晰地記得,自己家里當時就住進了兩戶從分洪區轉移出來的百姓,一住就是近一個月。無數像他家一樣的家庭,騰出住房,分享食物,成為了這場大轉移中最溫暖的后方。
然而,爆破的巨響最終沒有傳來。在最危急的關頭,中央決定,依靠萬千軍民嚴防死守荊江大堤,同時命令上游清江梯級電站在保證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盡可能多地攔蓄洪水,減輕荊江防洪壓力。
這是一個無比艱難的決定,也是一個創造奇跡的決定。
洪峰過境,大堤堅守住了,分洪區33萬百姓家園保住了,整個江漢平原安全了。
那一年,荊江分洪工程這張“底牌”,雖未翻開,卻已然驚心動魄。它讓世人看到了長江水患的兇險,也看到了中華民族在災難面前的堅韌與犧牲。
1952:“底牌”的使命
為何要建設如此大規模的分洪工程?答案藏在“萬里長江,險在荊江”這句老話里。
長江中游的荊江段,自湖北枝城至湖南城陵磯,九曲回腸,河道狹窄,水流宣泄不暢。每逢汛期,上游洪水與清江、沮漳河等支流洪水在此遭遇,極易泛濫成災。
位于荊江南岸的公安縣,更是“洪水走廊”的核心,境內18條河流穿行而過,自古便是“水漲輒成巨漫”之地。建縣2100多年,公安縣因水患7次遷城,僅1272年至1874年間,決堤就達58次之多。

▲荊江分洪區占據公安縣四成多的縣域面積 攝影:楊津
為了根治荊江水患,新中國成立伊始,便將荊江分洪工程列入第一個五年計劃。這是共和國歷史上第一個大型水利工程。
1952年春天,10萬軍人、16萬農民、4萬工人,總計30萬建設大軍,匯集于公安縣境內。在那個技術、材料極度匱乏的年代,建設者們面臨著難以想象的挑戰。
“當時機械化程度極低,混凝土澆筑需要的碎石,全靠人工錘砸。”荊州市荊江分洪工程南北閘管理處北閘管理所景區辦副主任張美琪介紹道。
一個工人一天僅能砸出0.2立方米碎石。挑戰之下,19歲的松滋女工辛志英發明了“鷂子翻身砸石法”,用草繩捆綁石塊,巧妙施力,創造了日碎石1.38立方米的最高紀錄,她也因此成為全國特等勞模。

▲荊江分洪工程進洪閘(北閘) 攝影:楊津
正是靠著這種沖天的干勁和無窮的智慧,建設大軍僅用75天,就奇跡般地建成了太平口進洪閘(北閘)、虎渡河節制閘(南閘)等一期主體工程。
隨后,18.48萬民工歷時5個月完成了剩余工程。這座用雙手和血汗筑起的鋼鐵屏障,將荊江的防洪標準從“十年一遇”提升至“四十年一遇”。

▲荊江分洪工程節制閘(南閘) 攝影:楊津
這座巨大的工程,主體由長1054米的北閘、長336米的南閘以及208公里圍堤構成。北閘54孔閘門,如鋼鐵衛士般佇立,最大泄洪量可達每秒8000立方米;南閘則以32孔弧形鋼閘門,精準調控著進入洞庭湖的水量。
1954:犧牲與勝利
這塊“底牌”,真正在實戰中被翻開,是在1954年。
工程竣工僅兩年,長江流域便遭遇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荊江大堤全線告急,在洪峰的輪番沖擊下岌岌可危。中央緊急批準,首次動用荊江分洪工程。
1954年7月至8月,北閘先后三次開啟,滾滾長江水咆哮著涌入分洪區。分洪最大流量達到每秒7700立方米,累計分洪總量122.6億立方米。分洪區內,17萬公安群眾在洪水到來前,背井離鄉,緊急轉移,眼睜睜看著即將豐收的莊稼和辛苦建起的家園,被濁浪吞噬。
這次巨大的犧牲,換來的是荊江大堤在險境中得以保全。分洪硬生生將沙市水位壓低了0.96米,最終化險為夷。它保住了江漢平原的千里沃野,更保住了武漢三鎮的安全。
這是荊江分洪工程建成至今,唯一一次大規模的實際運用。“舍小家,為大家”的精神也從此融入了這片土地的血脈。
2020:水大但心安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隨著2003年三峽工程開始蓄水發電,荊江兩岸的命運,迎來了歷史性的轉折。
“三峽大壩的建成,讓荊江兩岸迎來了真正的安瀾時代。”這是當地百姓最樸素也最深刻的感受。
能抵御百年一遇洪水的三峽工程,與作為“終極底牌”的荊江分洪區,構成了牢不可破的“鋼鐵長城”,即便面對千年一遇的洪水,也有了從容應對的底氣。
對此,親歷了“九八抗洪”的陳小明感觸極深:“以前上游稍微漲點水,我們這里就跟著緊張。三峽工程建起來以后,對洪水的調蓄功能有了極大的改善。”
數據是最好的證明。2010年和2012年,長江上游兩次發生超1998年洪峰量級的特大洪水,三峽水庫通過精準的“削峰”操作,將超過每秒7萬立方米的洪峰,削減至每秒4萬立方米左右下泄,使沙市水位始終控制在43米的警戒水位之內,荊江分洪區安然無恙。
2020年8月,長江形成歷史罕見的第5號洪水,洪峰流量高達每秒78000立方米,遠超1998年。面對如此嚴峻的考驗,三峽工程累計攔蓄洪水295億立方米,再次實現了分洪區的“備而不用”。公安縣分洪區內的60萬群眾無需轉移,49.3萬畝耕地和10余萬畝水產養殖區得以保全。

▲?2020年8月20日,三峽樞紐迎來建庫以來最大洪峰。按照防汛調度指令,三峽樞紐開啟11個泄洪孔洞,出庫流量按49200立方米每秒下泄,削峰率達34.4%。?攝影:陳臣
“三峽工程大大降低了分洪的可能,”付兵感慨道,“以前一到汛期,分洪區的群眾心就揪著,現在要到‘千年一遇’才有分洪可能。分洪的幾率小太多了,老百姓心里的恐懼感慢慢消失了,能夠長時間地安居樂業。”
這種安全感,深刻地改變了荊江兩岸的生產生活方式。過去因擔心隨時可能到來的洪水,農業生產多為零散種植。如今,一望無際的連片水稻、油菜花田成為江漢平原的壯麗景觀,公安縣的農產品也形成了規模化經營,產量穩定增長。旅游、水利配套等產業興起,越來越多的外出務工人員選擇返鄉,開辦農場、經營民宿。
2025:汛期的游客
夕陽下,靜靜佇立的北閘,與長江對岸的荊州萬壽寶塔隔江相望。江水安瀾,歲月靜好。
如今的北閘,早已不再是那個讓人談之色變的“泄洪口”。在確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它有了一個新的身份——國家AAA級旅游景區。游客們來到這里,觸摸著“新中國水利第一閘”的鋼鐵之軀,在講解員的講述中,聆聽1954年的分洪往事和1998年的驚心動魄。

▲?靜靜守衛家園的荊江分洪工程北閘,如今已是國家AAA級景區。 攝影:楊津
景區內,一座建于1952年的“金江亭”尤為引人注目。亭身巧妙地融入了鐮刀、錘子、五角星等紅色元素,亭旁矗立著毛澤東主席“為廣大人民的利益,爭取荊江分洪工程的勝利”和周恩來總理“要使江湖都對人民有利”的題詞碑刻。這些字跡,穿越了70多年的風雨,已成為這片土地賡續傳承的紅色基因。
盡管分洪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但作為“底牌”的使命,荊江分洪工程從未被遺忘。
“我們每年都會嚴格按照規程,進行三次閘門啟閉演練。”張美琪介紹說。當年需要8人合力才能轉動的人力絞盤,如今已被現代化的啟閉機取代,但手動操作的功能依然保留。管理所的每一個人,都必須熟練掌握開閘的全部技能,只為在關鍵時刻能正常啟用,守護荊江兩岸的安全。

▲荊江分洪工程進洪閘閘門啟閉機 攝影:胡暉
從無奈的犧牲,到有備無患的從容;從“洪水走廊”的千年憂患,到三峽護航下的歲歲安瀾。荊江分洪工程的故事,是中國人民治水史詩的一個縮影。它和它所守望的土地,共同見證了一個國家從“人定勝天”的抗爭,到“人水和諧”的跨越。
那張深藏的“底牌”依然在那里,而因為有了三峽工程這張更強大的“王牌”加持,千萬江漢兒女,將一份波瀾不驚的泰然,刻進了生命的底色。
編輯:任賢 楊思恒 盧西奧
發布日期:2025年09月26日